設想,在北京二環主路上發生了一起兩車相撞的交通事故,兩名車禍受害者都身受重傷,這時候交警趕到現場調查事故原因。其中一個受害者告訴警察:“警察同志,我不知道那車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我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第二個受害者說:“警察同志,用您的執法系統查一下我的車牌,碰撞錄像和遙測數據應該已經自動上傳到警務系統了。”

極度智能的交通工具在成功商業化后對交通安全意味著什么?這些強大的智能控制策略是離不開龐大的統計數據的,而冷冰冰的數據又能怎樣幫助減少交通事故的呢?
自動駕駛技術成功地將交通事故轉化為了交通錯誤。它成功地把交通事故的不可預測性以及由于人類駕駛員非理性狀態下行為的不可控性大大降低了。在可量化、可建模、可分析的架構下,實現了如同函數般精準的數學表達。
這就是為什么自動駕駛技術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汽車安全史上最偉大的創新。因為人類終于有機會對“不可測”事件實現預測和分析。
在美國,2016年一整年的交通事故是700萬起,即便是最負責任的交警和最認真匯報交通意外的當事人也無法完整提供詳盡的事故報告。我們能知道的最詳盡的數字就只有700萬,誰都無法觀察到在事故發生時當事人的情況,更無法量化其中的變量。
根據NHTSA(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的報告,29%的事故當事人完全無法給警察提供任何有用的事故信息,就如同文章開頭的第一位事故當事人那樣。而這個數字,放在2017年的全年自動駕駛汽車的事故調查中,是0%。
原因很簡單,首先,測試的自動駕駛汽車并不多,基數不大;其次,駕駛員不需要記得發生了什么,傳感器、激光雷達、ECU模塊、行車電腦已經替他回答了所有問題。
在傳統汽車的話語體系中,駕駛員的駕駛技術(駕駛技術一定程度上和駕駛時間、年齡成正相關)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安全特征,沒有之一,要不然也就不會有“老司機”這樣的美譽了。但是老司機和菜鳥的駕駛策略是無法量化成為數學模型以供科學分析和預測的,唯一的一個可供參考量是年齡:20歲以下比20歲以上的汽車司機發生死亡交通事故的概率高三倍。即便是在20歲以下的司機群體中,16-17歲的青少年發生死亡事故的概率也是18-20歲的兩倍。
相比之下,自動駕駛技術可以把這個年齡差別造成的死亡率差別抹掉,創造一個更“公平”的受害者年齡分布,這算是一個小小的道德勝利。與此同時也把交通事故和駕駛技術之間的關聯打消了。
不僅如此,更加聰明的智能駕駛軟件和操作系統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汽車本身故障所引起的交通事故。在越來越高的數字化控制中,檢測車輛的機械故障、維修需求、材料疲勞甚至道路缺陷都成為可能,這使得駕駛員所需要監控的變量越來越少,甚至到最后不需要做出任何判斷。
如此,并可以將駕駛員對交通的影響因素降低到最小,每一臺在道路上行駛的車輛的穩態都是可控且可預測的,這對城市的道路管理和交通指揮也帶來了巨大便利。
在過去,交通事故的成因幾乎無法研究更無法完全判斷,就像我們的祖先面對雷雨閃電以為是某種神奇的力量。現在,當智能駕駛足夠普及,在道路上奔馳足夠安全時,那些冷冰冰的數據應該可以很快給人類做出一個合理的交通解密。
這一天到來,人類的交通會更加安全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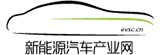
 登錄
登錄



